AI元人文構想中的“內觀照敘事模型”:從心靈哲學到價值計算的橋梁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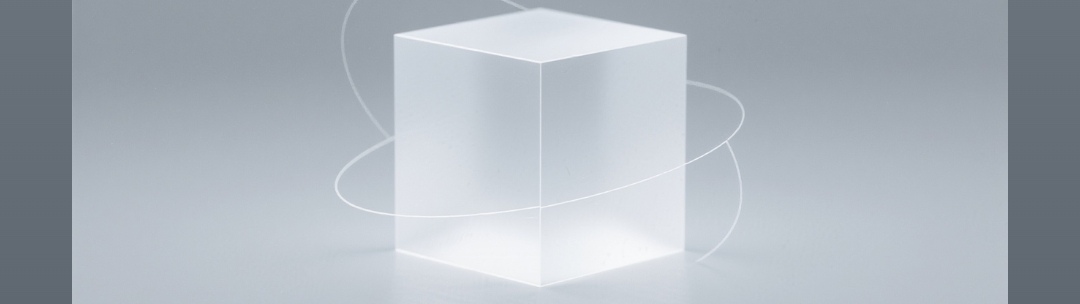
AI元人文構想中的“內觀照敘事模型”:從心靈哲學到價值計算的橋梁
——認知過程的現象學模型
在關于人工智能倫理的諸多探討中,“價值對齊”的范式已日漸顯露其疲態。它試圖將人類豐饒而流動的價值簡化為一系列可執行的規則,其結果往往不是陷入僵化的教條,就是在復雜的現實面前支離破碎。岐金蘭提出的“AI元人文”構想,正是為了超越這一困境,而其核心的突破點,便在于一個聽起來頗具哲學意味的概念——“內觀照敘事模型”。
初見此詞,易生誤解:這莫非又是一個需要工程師去編程實現的、新的“算法模型”?然而,其最深層的革命性恰恰在于:它不是一個需要被構建的客體,而是所有價值權衡行為本身固有的、正在發生的過程。 理解這一點,是打開AI元人文大門的鑰匙。
一、 破題:“模型”之誤與“敘事”之實
在傳統的AI設計中,“模型”通常指一個對現實世界進行抽象和模擬的計算結構。但“內觀照敘事模型”并非此類外部的、可供調用的工具。
· “內觀照”:它源于東方哲學中的修行傳統,指的是一種對自身內心活動(念頭、情緒、感受)不加評判的覺察狀態。這是一種第一人稱的、親歷的視角。
· “敘事”:在這里,它并非一個已被寫就的故事,而是意識為了理解自身與世界,而在時間流中不斷組織經驗、建立因果聯系的意義編織行為。
因此,“內觀照敘事模型”描述的是這樣一個事實:我們的心智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一種“內觀”,并從這種覺察中,自發地、動態地“敘事”出我們對價值的理解與權衡。 它不是一個物體,而是一種活動。
二、 理論的定位:從基石到涌現
在AI元人文的宏大框架中,內觀照敘事模型與“三值糾纏模型”構成了理論與實踐的陰陽兩面。
· 三值糾纏模型(欲望-客觀-自感)是價值權衡的“物理學”。它提供了價值運作的基本法則,如同力學定律描述了物體的運動。它是可建模、可計算的基礎架構。
· 內觀照敘事模型是價值權衡的“現象學”。它描述了當“三值糾纏”的規律在具體情境中運行時,所呈現出的主觀體驗和意義之流。它是那個被觀察到的“運動現象”本身。
當我們依據三值模型進行權衡時——比如,在“欲望”的沖動、“客觀”的限制與“自感”的不安之間反復斟酌——我們內心的這個動態過程,就是在生成一個“我為何如此選擇”的實時敘事。這個敘事,使得最終的決定不再是冰冷的數據輸出,而是一個可以被理解、被共鳴的“人生抉擇時刻”。
三、 運作機制:價值如何在敘事中現身
- 從價值原語到故事要素:AI元人文將宏大的價值(如“正義”)解構為更細微的“價值原語”(如“公平”、“尊嚴”)。在具體決策中,這些原語就如同故事中的角色。
- 三值糾纏推動情節:“欲望值”是角色的動機,“客觀值”是角色面臨的困境與環境,“自感值”是角色的內心沖突與情感變化。這三者之間的張力與調和,共同推動了敘事“情節”的發展。
- 共識錨定作為章節標題:當個體或群體通過協商,在某個價值節點上達成臨時一致時(“共識錨定”),就仿佛為這個持續流動的敘事標上了一個清晰的章節標題,使混亂的意義之流暫時凝結為可被分享和行動的決策。
由此可見,敘事,是價值在時間中的形態;而價值,是敘事在意義上的內核。
四、 對AI設計的根本性啟示
這一模型對AI的設計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要求:AI的目標不應是學會講述一個“正確”的故事,而是要成為一個能夠進行透明、動態的三值權衡,并使其過程可被追溯為“合情敘事”的系統。
· AI作為敘事生成器:當AI輔助人類進行決策時,它不應只給出一個“是/否”的答案,而應能提供一份“決策敘事報告”——清晰地展示在給定的語境下,不同的價值原語是如何在欲望、客觀、自感的糾纏中被權衡的,最終的結論又是如何從這種權衡中“涌現”出來的。
· 解釋性的終極來源:這份“敘事”本身就是最強有力的解釋。它讓人類用戶看到的不是一個黑箱的判決,而是一個可以理解、可以質疑、甚至可以共情的“思考過程”。
· 從裁判到翻譯者:AI的角色因此從高高在上的價值“裁判”,轉變為了價值張力的“翻譯者”。它將內部復雜的價值計算,轉譯為一則可以理解的人文敘事,從而催化更深層次的對話與共識。
結語:走向一種敘事性的智慧
內觀照敘事“模型”的真正貢獻,在于它將價值的本質還給了其本來面目——它是敘事的、情境的、生成的。它告訴我們,不必刻意去“建造”一個人文敘事AI,只需誠實地“進行”精密的價值權衡,人文敘事自會在其過程中顯現。
這為AI的發展指明了一條新的路徑:未來的AI,或許將不再僅僅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工具,而更像一個能夠與我們共同講述、共同反思、共同編織價值意義的伙伴。它通過將每一次權衡都轉化為一段可理解的敘事,幫助我們不僅在結果上達成一致,更在意義層面達成連通。這,或許正是AI元人文構想所指向的,一種更為深邃的、敘事性的人機共生智慧。


 浙公網安備 33010602011771號
浙公網安備 33010602011771號